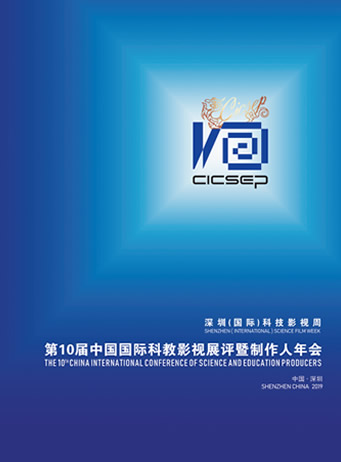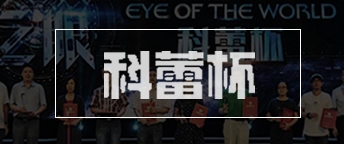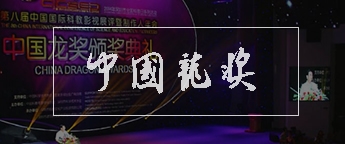摘 要
贾樟柯的电影作品中大量运用了纪录片的拍摄方法,他的电影与纪录片时常呈现出“互构”关系,既互相补充又互相辅助,共同完成叙事。通过对纪录片理念与方法的融合运用,贾樟柯描绘出社会转型的巨变和普通人的心灵史,重新诠释了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他喜欢讲述普通人的故事,把对于个体生命的尊重作为前提并且加以强调,从“人”出发,进而关注社会的状况,对现实进行自省与批判,这也使得他的作品具有鲜明的现实性与人文性。这种关注“人”的人文主义与纪录片精神,也成为贾樟柯电影美学思想的精髓。他努力发掘那些游走于现代都市文明边缘的普通人的人性尊严,透过极具纪实性与风格化的电影语言,构造起独特的“乡愁的诗学”。
关键词
转型期;乡土社会;纪录片精神;人文主义;乡愁诗学;个体叙事
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贾樟柯都是中国电影界一个特别的存在,他犹如一株扎根于乡野民间的野草,兀自生长、别无他顾,敏感尖锐又饱含忧伤,在众声喧哗的商业浪潮中执拗地坚持艺术电影的原则,坚持讲述普通人的心灵史。贾樟柯开始拍摄电影始于1997年,那正是中国经济经历快速发展的时期,电影产业化、商业化浪潮日益盛行。而贾樟柯在作品中所流露出的艺术风格,却和当时的整个社会文化方向背道而驰,这使他无意间成了一个商业文化的反叛者,一个不向商业妥协的独立电影人。在对自己的职业定位和自我认同上,这位来自山西汾阳的电影导演,毫不掩饰自己的乡土背景,谦逊地把自己称为“一个来自中国基层的民间导演”。从第一部作品《小武》起,贾樟柯的电影就不断地在各类国际影坛中斩获奖项,而他一系列杰出的电影成就,都与他独特的电影美学思想密不可分。
一、现实性与人文性的书写:普通人的心灵史与个体叙事
贾樟柯是中国电影界一位少有的有良知、有勇气、有独立思考力的创作者,他通过一部部电影和纪录片作品犀利地审视着当下的中国社会现实,用一颗饱含深情的赤子之心,默默地关注着那些习惯了被遗忘、被忽略的普通人,以及他们深藏在历史深处的忧伤与叹息。在二十多年的创作生涯中,贾樟柯用影像描绘出了转型期中国所经历的巨大社会变迁图景,以及在此过程中社会关系的变化和普通人个人命运的转向。当中国电影的审美品位被好莱坞流水线、商业化浪潮不断裹挟,电影界创作的主流力量频频流连于历史传奇和虚构神话题材的时候,贾樟却将目光投向了正在经历巨大变革的中国社会现实。在这样的背景下,他的一系列作品所体现出的强烈的现实关照性和人文精神就显得尤为可贵。贾樟柯曾经直率地指出过当代中国电影在创作题材上的一个缺陷,那就是缺乏对人的真实生命的关注。中国电影第四代导演在创作上过分关注电影本体之上的伦理道德,第五代导演在题材选择上过于执着于虚构的历史寓言,而第六代导演则大多沉醉于现代都市摇滚类型电影。
在贾樟柯看来,创作态度比表现形式更为重要,因为用什么方法拍电影取决于用什么态度看世界。 这种对现实生活不回避不矫情不神话的创作理念,使他获得了一种更加本真与自由的叙事状态。从第一部电影起,贾樟柯就表现出了对中国当下社会现实的强烈关注与自省。他喜欢将镜头对准社会现实中的一个个普通人,讲述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因为“经历这个时代的个人是不能被忽略的”。贾樟柯说,他尊重普通人的真实生活,他想通过电影关注普通人,表达每个生命的喜悦或沉重。 透过独特的影像叙事,贾樟柯执着于讲述那些时常被宏大叙事、历史传奇所回避、忽略甚至是过滤掉了的普通人的真实生活,尤其是边缘人群的日常生活和心灵历程,把对于个体生命的尊重作为前提并且加以强调,从“人”出发,进而关注社会的状况,对现实进行自省与批判。正是这种关注个体生命价值与尊严的人文主义创作立场,使得他的作品总是洋溢着浓厚的悲悯情怀,以及直面现实、直抵生命的真实感与穿透力。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乡土社会开始受到城市文明的冲击。贾樟柯敏锐地捕捉到了城乡碰撞所带来的种种变化。随着物质环境的改变,乡土社会关系、道德伦理观念、生活方式都在面临新的挑战,传统田园牧歌式的“故乡”形象开始消解。然而,他真正想要关注的并非社会层面的宏大叙事,而是透过社会层面的种种变化,挖掘与讲述隐藏在宏大历史背后的人的个体生命经验。 他努力发掘那些游走于现代都市文明边缘的普通人的人性尊严,透过极具纪实性与风格化的电影语言对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社会与普通人的命运转折进行了冷静的描绘与反思,细腻地展现了社会变迁中普通人面对的种种冲突与困境。贾樟柯曾经坦言,纪录片精神中有一种人道精神。 而这种真实、平等、公正、人道主义的纪录片精神,也正是他想要透过影像表达的对具体的“人”的现实关怀。对社会现实和普通人的关注,尤其是对底层边缘人群的心灵关怀,使得他的电影具有一种深刻的思想性和社会学价值。
二、真实与虚构的艺术:纪实性与叙事性
(一)纪录片与电影的互构
在贾樟柯早期的作品中,剧情电影占了大多数。作为一名擅长拍摄剧情长片的导演,他也显露出对于以纪实性为特征的纪录片的偏爱。除了像《小武》、《站台》、《任逍遥》、《三峡好人》、《山河故人》这些典型的剧情片之外,贾樟柯还拍摄过《公共场所》、《无用》、《东》、《二十四城记》、《海上传奇》等多部纪录片。在传统的电影媒介观念中,电影与纪录片在拍摄理念与手法上往往有着严格的划分,然而当人们观看贾樟柯的影像作品时,却时常惊叹于他对这两种体裁的融合运用。在贾樟柯的多部电影中,观众可以看到他对纪录片拍摄手法的大量运用,而在他的诸多纪录片作品中,人们也可以看到他对故事化叙事的娴熟运用。
电影创作倾向于故事化的虚构叙事,纪录片创作则以真实感、纪实性见长,贾樟柯擅长将这两者融合运用。因此他的纪录片作品与电影作品时常呈现出一种隐秘而微妙的“互构”关系,两者在美学观念与制作手法上既互相补充又互相辅助,共同完成叙事。在他看来,纪录片是帮助人类和遗忘对抗的一种方法, 适合展现人的真实状态,而纪录片中人物刻意回避的一些不好言说的部分,却恰恰是故事片发挥的空间。 在他早期的剧情电影《小武》、《站台》、《任逍遥》中,洋溢着一种强烈又真实的现场感和纪实性。贾樟柯说,在拍摄之前他就已经确立了一种来自纪录片的创作思路,有意识地想把这三部电影做成“故乡三部曲”,实现只有纪录片才能达到的美学效果。
贾樟柯剧情电影中常用的纪录片创作方法主要体现在使用非职业演员,大量运用长镜头,以及时常采用非常规的叙事结构等方面。在贾樟柯的第一部剧情长片《小武》中,为了还原生活本身那种粗糙的真实的质感,他采用了DV摄像机手持拍摄的方式,使用了抓拍、抢拍等纪实拍摄的方法,还有意剪辑了许多晃动不定的镜头,并要求他的录音师在电影中加入更多喧闹的环境音。在谈及此种处理方式的初衷时,贾樟柯说这源于他对基层民间生活的真实体验。他想表现出影片中的人物如何在一种具体的条件下人性地存在。 可见,贾樟柯是在有意识地运用源自纪录片纪实传统的理念与手法,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方式构建极具个人风格的电影美学。与曾经流行的批判现实主义相比,贾樟柯的叙事更为沉静和不张扬,他在电影中从不做简单的道德判断,而是惯于运用纪录片的手法,将强烈鲜明的纪实性风格融入情节叙事, 描绘出人物生动鲜活的生命经验,在缓慢流淌的时间中雕琢出别具韵味的日常生活美学。
(二)镜头语言的纪实性
借助纪录片的多种美学手段,贾樟柯着力强调的是生活的真实与生命的真实,这其中不仅包括了社会现实的真实,更包括了人物生存状态、命运和情感的真实。基于这样的理念,他在长期的拍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不拘一格的拍摄方法和风格化的镜头语言。比如在电影拍摄中,贾樟柯经常会打破常规,记录下生活中真实发生的场景,然后将这些纪实段落穿插到电影的叙事线中。比如在电影《小武》的开场,他就记录下了这样的镜头——一个乡村家庭在公路旁候车,准备送别他们的女儿。这个影像属于拍摄时捕捉到的众多旁观者的镜头之一,贾樟柯说,因为这个真实场景所透露出的“离别的悲哀”深深触动了他, 他才会把这个意外捕捉到的片段,用在了影片的叙事结构中,而像这样的例子在他的电影中还有许多。
首先,在镜头语言上,贾樟柯十分强调镜头的距离感与生活感。在拍摄现场,他十分注意摄影机的位置,常会寻找一个合适的拍摄位置,设定一个合适的距离来观察空间内的人物。这种有意使摄影机与被摄对象保持恰当的距离的方法,是为了让消除人物的紧张感,保持一种自在舒服的状态。这样可以使导演在时间的积累中,慢慢用镜头去捕捉空间、情境和人物的真实气息。 在谈到这种工作方法的时候,贾樟柯解释,距离感会直接影响到拍摄和被拍摄者之间的关系。他的这个拍摄习惯,是为了不让被纪录者意识到摄影机的存在,因此他尽量不与他们交谈或者干预他们。在贾樟柯看来,导演通过这种人为的有距离的设置,得以观察人物的状态和心理,从而调动起观众的生命体验,对人物的处境和情绪感同身受。也就是说,创作者提供的影像是可以调动他人的记忆和生命经验的。 那么,怎样才能调动起观众的生命体验呢?贾樟柯的方法就是依靠一种客观中立的观察视角与距离感来塑造影像世界的空间维度上的“真实”。在空间上与人物保持一定的距离,这种视角符合了普通人在日常生活中观察、接触他人的习惯,因此也会唤起观众空间层面“身临其境”的同在感,并激发观众在情感层面与主人公产生“共情”。从这个角度说,“真实感”的营建可以帮助观众对电影叙事产生强烈的认同感,从而调动起自身生命经验,带着自己的记忆与情感主动参与到叙事中,激发更深层面的“情感卷入”。
其次,贾樟柯还强调用镜头语言塑造完整的时间与空间。出于对“距离感”和“真实性”的强调,他十分偏爱长镜头,在几乎每部作品里都大量运用了长镜头,而这也成为贾樟柯电影镜头语言的一种鲜明标识。通过这些游移摇曳的长镜头,他细腻地捕捉到了隐藏在缓慢时间和静止空间之下的人的真实状态,从而形塑出一种连续而完整的叙事时空。在谈到长镜头在他作品中作用的时候,贾樟柯说过,他偏爱长镜头是为了不对观众的凝视进行掌控并维护他们的观影自主权,因为长镜头可以使摄影机和被摄者之间保持一种有距离的观察,从而帮助导演更为客观地展示特定时空中的人和事物,并使事件得以自由、不受干扰地展现。 长镜头的语言特性,它的连续拍摄与自由运动,能帮助贾樟柯更好地塑造影像世界中的时间与空间,并保持时间与空间的相对完整性。
在对距离感、真实性近乎偏执的坚持背后,贾樟柯透过镜头语言所要表达的,其实是一种客观的视角与中立的态度,同时也反映出他对构建影像世界的时空有着自己十分独到的理解。他用纪录片的方法与精心设计的镜头语言所构筑起的是这样的一种时空观——那就是注重和强调时空的真实性与完整性。而贾樟柯之所以如此看重时空的真实性,以及故事所蕴含的生活逻辑和人物情感的真实性,其实都源于他想传达一种“平等、尊重个体、渴望自由的意识价值观”。
(三)建构历史的叙事策略
贾樟柯在拍摄纪录片的时候,经常会运用故事化的叙事策略。为了还原已经过去的历史,他在片中经常会运用“搬演”、“再现”等叙事手法,还常会设计一些戏剧化的桥段,加到叙事结构中去,以增强故事性和情节性。比如在纪录片《二十四城记》中,贾樟柯在大段真实的人物访谈中,穿插进了由演员陈建斌、吕丽萍所扮演的人物访谈。而在纪录片《海上传奇》中,为了展现上海百年历史与个人命运紧密交织的戏剧性,他进行了故事化的设计,在一段段真实的人物访谈段落之间,穿插进了演员赵涛在上海的街道、废墟间游走的镜头,并由此串联全片,贯穿始终。这种独特的叙事策略向观众展示了贾樟柯是怎样在纪录片的记录中加入艺术化的虚构手法,并由此构建起历史“真实”的过程。这种还原历史的处理方式,可能会让许多人感到难以理解,然而对叙事“真实性”的问题,贾樟柯有着自己的理解。他认为电影中的真实并不存在于任何一个具体而局部的时刻,而是存在于结构起承转合的联结之处,是在拆解叙事模式之后仍然让人信服的一种现实秩序。一切纪实的方法都是为了描述创作者内心经验的真实世界,即“经验现实”,而非客观存在的物质现实。由于人无法真正地接近“真实”本身,因此电影的意义不仅仅是为了达到对现实的描摹这一层面。贾樟柯所追求的是一种电影美学层面的“真实感”,甚于追求社会学层面的现实真实。
在贾樟柯看来,一切纪实的方法都是为了描述内心的经验。“艺术的真实”源于生活的真实,却又不完全是客观世界的照搬,而是人内心经验世界中的“真实”。也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贾樟柯才会在纪录片中使用再现、想象等虚构化的叙事策略,让这些叙事策略参与到现实记录中来,用多元化的视觉再现方式共同构建起历史的“真实”。相反,他同样会在戏剧化的叙事结构中,突然穿插进一段人物日常生活状态和内心情感的真实记录,以此营建叙事的“真实感”。可以说,贾樟柯的电影作品时常跨越剧情电影与真实纪录片之间的边界,瓦解了“真实”与“虚构”之间的二元对立,而这也是为什么贾樟柯的电影常会呈现出一种多元混搭风格的原因。我们在他塑造的影像时空中时常能够看到,故事化的虚构叙事与纪录片的真实记录之间的自由切换与穿梭,以及“历史”与“虚构”、“真实”与“想象”,这些原本二元对立的观念是怎样突破彼此的边界,完美融合在一起的。无论是充满冲突和张力的戏剧性,还是冗长琐碎的日常情境中的真实性,无论是历史断裂中的荒诞性,还是想象世界里的真实性,这些看似矛盾对立的概念和属性,通过贾樟柯创造性的视觉再现,向人们揭示出了这样的一种后现代主义电影美学思想——我们需要重新定义那些看似断裂、疏离,实则紧密结合又无法分割的视觉元素,以及它们参与构建影像时空的方式。
三、结语
在激荡的城乡巨变中,贾樟柯敏锐地捕捉到了湮没于现代化浪潮深处的故乡的别离与乡愁,以及被宏大历史叙事所忽略的普通人的个体生命经验。在他的电影中,故乡生活的再现虽然是在现代化过程中被瓦解和破坏的,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停滞的,然而贾樟柯却在其中发现了某种诗意与乡愁。 贾樟柯二十多年的创作实践都是在构造一种“乡愁的诗学”。 在二十多年的电影创作中,贾樟柯通过纪录片方法的实践,忠实纪录下了社会转型的巨变和普通人的心路历程,构建起独特的电影美学体系。他的作品注重“平等与公正,以及对命运的关注和对普通人的体恤之情”, 这种关注“人”的人文主义与纪录片精神,也成为贾樟柯电影美学思想的精髓。在商业电影席卷市场的浪潮下,贾樟柯依然坚持着艺术电影的原则,保持着创作的独立性。从早期的故乡三部曲,到后来的《任逍遥》《世界》《二十四城记》《海上传奇》《天注定》《山河故人》,他的作品逐渐成为世界了解当代中国的一种方式。贾樟柯重新诠释了中国电影的现实主义。正如美国电影导演马丁·斯科塞斯所评价的那般,“每隔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总会有人出现并重新发明电影……他重新发明了电影。”
注释
1.徐雪芹:《当代中国咏叹者贾樟柯》,《电影》,2012年第11期,第45页。
2.贾樟柯:《贾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0页。
3.贾樟柯:《贾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9-31页。
4.贾樟柯:《贾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0页。
5.贾樟柯:《贾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8页。
6.贾樟柯:《贾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50页。
7.贾樟柯:《贾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26页。
8.贾樟柯:《贾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4页。
9.贾樟柯:《贾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7-58页。
10.徐雪芹:《当代中国咏叹者贾樟柯》,《电影》,2012年第11期,第45页。
11.蒋原伦、史健主编:《先锋,对话:我们已经选择》,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第35页,转引自[美]白睿文(Michael Berry):《乡关何处: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连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40页。
12.贾樟柯:《贾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32页。
13.贾樟柯:《贾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43页。
14.[美]白睿文(Michael Berry):《乡关何处: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连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6页。
15.贾樟柯:《贾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9-100页。
16.欧阳江河主编:《中国独立电影访谈录》,四川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268页,转引自[美]白睿文(Michael Berry):《乡关何处: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连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21页。
17.[美]白睿文(Michael Berry):《乡关何处: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连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2页。
18.贾樟柯:《贾想》,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5页。
19.[美]白睿文(Michael Berry):《乡关何处:贾樟柯的故乡三部曲》,连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0页。
相关新闻